2024年8月18日,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、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对谈,带领我们重返生气淋漓五四时代,与我们共同对话关键时刻、关键人物、关键学说。

陈平原:我讲的主题为“为何以及如何与五四对话”。
我二十年前曾说过:
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你都必须认真面对,这样,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,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。…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,“五四”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。作为后来者,我们必须跟诸如“五四”(包括思想学说、文化潮流、政治运作等)这样的关键时刻、关键人物、关键学说,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。这是一种必要的“思维操练”,也是走向“心灵成熟”的必由之路。
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辩证。中国学界一般容易把“新文化运动”和“五四运动”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谈。广义来说可以放在一起,但是仔细斟酌是不一样的。若谈论新文化运动,尽可能往上走,从晚清说起;若辨析五四运动、五四精神或五四时代,则最好往下延伸,仔细倾听那些遥远的回声。往前追溯,从晚清说起,主要是史学研究;往后延伸,牵涉整个二十世纪,更侧重思想操练。或者说,谈论小五四(指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),重在考证与还原;研究大五四(指作为思想潮流的五四时代),关键在于阐释与介入。
我的“五四研究三书”,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直接面对,《“新文化”的崛起与流播》往前追溯,《未完的五四》往后延伸。之所以选择三种不同路径,基于五四话题本身的丰富性、复杂性与现实性。这次北大出版社出的《未完的五四》是我几年前《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》的增订版,做了比较多的调整,和学院派专业论述不一样,带有论战性质,单刀直入,谈我心目中的五四。而这个话题本身今天仍有意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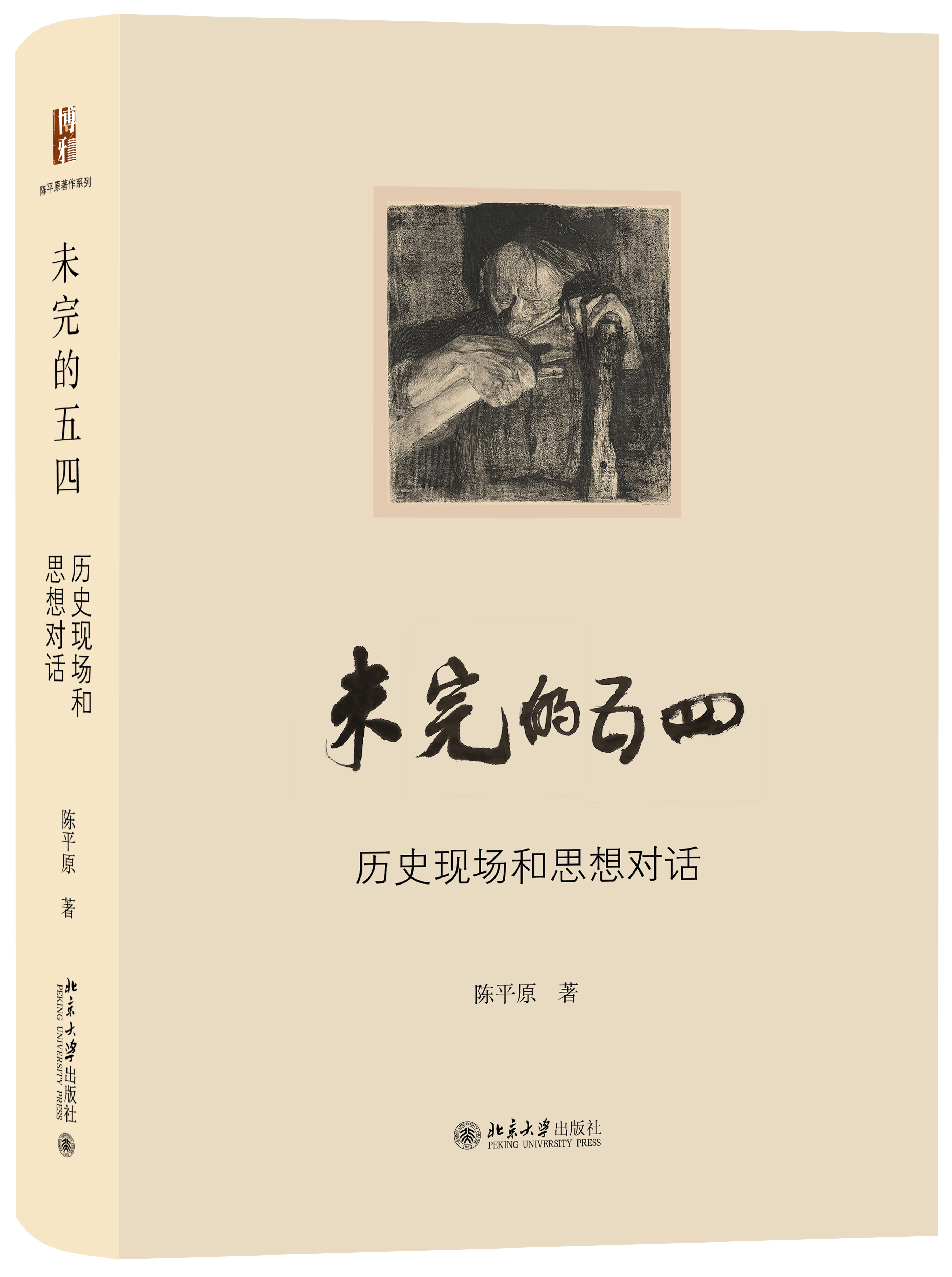
陈平原著《未完的五四: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》
几年前《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》出版,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做了一次专题讨论会,谈到一个话题:我们这代人有没有能力、有没有需要、有没有机缘不断地和五四对话。其实每代学者、每个学者都有自己内心压在纸背的心情,借助五四这个话题得以呈现。所以我才会说,把五四当成砥砺思想学问的磨刀石,不在于本身具体论述的对错,而在于借助这个话题可以展开很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。
为何不断和五四对话?五四在研究近现代文学的人看来,毫无疑义是正面的话题,可是整个社会并不是这么考虑问题。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跟很多人辩论,很多大学校长觉得五四搞砸了,如果没有五四,五千年中华文明就不会断裂,甚至有些人故意把五四和二十世纪的激进运动联系起来。我们怎么看待传统,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连续与断裂,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,这些话题都是有挑战性。专业研究者要面对社会上的很多的挑战。
两三年前,北大开启了一个校友终身学习计划,第一讲选择我的《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》,我当时只是把课堂内容略微总结一下,面对全球的北大校友,做线上的讲座。后来学校说居然有三十六万人在听,估计也有校外的朋友在听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甘琦一听,一定把这个重新做成一本书,所以我才做了这么大的调整,书名“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”,她觉得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有点绕。其实那是上海社科联组织的专题会议的论文,我觉得写得不错,但是非专业的读者可能不容易接受,所以最后我们敲定书名为“未完的五四”:未完成、未完美、未完结、未完待续,这是我们心目中的五四。香港版的封面设计都往这个方向靠拢:想象中国是一台旧电脑,蕴涵巨大的思想资源,刚打开一点,有很多内存还没有打开,有思想之源,但是不见得能真正地接受和打开,我们的工作是让一代代人激活那个内存,让我们得以不断地跟五四进行对话。
五四的未完成、未完美、未完结、未完待续,大家会觉得不是特别好理解,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,以便于大家理解,我心目中的五四为什么是这样子。

陈平原
我有一篇长篇文章《新文化运动的正面、侧面与背面》,其中关于思想史、文学史及教育史视野中的五四、蔡元培、陈独秀、胡适等人的故事,只是在原有论述基础上深描,没有惊人之语。值得推荐的是关于林纾的性格、“两位不幸的北大学生”,以及“闯进瓷器店的大象”的部分。
对于非专业读者,如果想知道五四是什么样子,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减法,请你以这三篇文章为中心阅读思考:第一篇陈独秀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,谈德先生、赛先生;第二篇蔡元培《致〈公言报〉函并答林琴南函》,大学循思想自由原则、取兼容并包主义;第三篇胡适的《新思潮的意义》,研究问题,输入学理,整理国故,再造文明。这三篇文章都发表于1919年,这三篇文章读进去,就知道思想、精神、文化层面的五四是什么样子。
所有谈北大的文章都会提到蔡先生的兼容并包。作为大学校长,主张兼容并包,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,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。学界普遍认定,正是蔡氏主校后的所作所为,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。乐于传诵蔡氏容纳异己之雅量者,必须同时考虑其坚持原则时的倔强与不肯通融。有一个故事是辜鸿铭和林纾。这是蔡先生自己在文章中提到的。《觉醒年代》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辩证,让大家重新了解辜鸿铭,以前都是把辜鸿铭当作负面人物看待。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,蔡先生1919年说,“我们不会因为他是提倡帝制就不聘他教英国诗歌”。第二年辜鸿铭却被解聘了,因为学生告状,谁告的?罗家伦,因为他在上英国诗歌,可是大部分时间在骂新文化,这不像教书的样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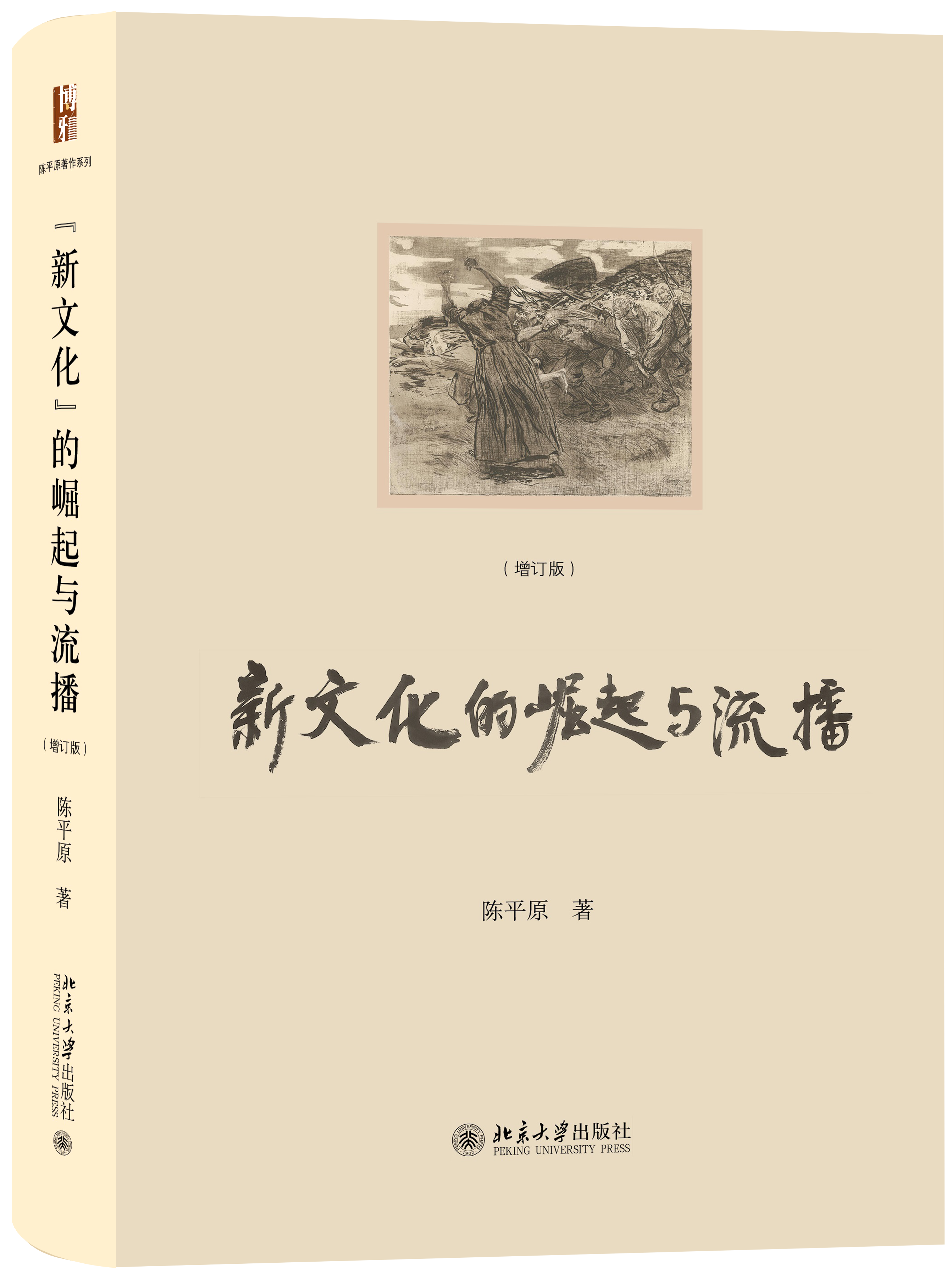
陈平原著《“新文化”的崛起与流播》(增订版)
所有学新文学的人都记得一件事,林纾写过《荆生》《妖梦》两篇小说,我想做一个补证。对林纾的研究最近十年二十年有拓展,包括他的心态、论文、长篇小说、其他的若干诗文写作。其中讲到林纾的性格以及游戏笔墨。因为谈新文化经常会提他为了反对新文化而写了《荆生》和《妖梦》,目的是动用军阀的力量扼杀新文化运动。因为林纾在北京教书时,有学生徐树铮成为军阀。这个论述在今天的五四运动史或者新文学的著作里会提到。我的解释是,这个说法子虚乌有,是新文化人的哀兵之计。
日后的研究者越说越实,把一篇子虚乌有的小说,说成了货真价实的战书。如果林纾有阴谋,不应该写小说,从北京寄到上海发表,动员别人采取军事行动,而应该是密谋。这必须回到林纾本人的性格,他自幼学剑,“少年里社目狂生,被酒时时带剑行”。再加上撰有记录闽中武林轶事的《技击余闻》,还有《剑腥录》中吹嘘邴仲光如何仗剑行侠,这“伟丈夫”实为林纾的自我期许。日后史家也懒得仔细追究,林纾“勾结军阀铲除异己”的罪名,就这样被派定。
一场大的思想文化运动,在其展开的过程中,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,有人赞成有人反对,这都很正常。日后某种声音占了上风,取得决定性胜利,不等于反对者就是敌人,或者“大逆不道”,是要唾弃的敌人。凡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参与对话的,不管立场左中右、声音高中低、力量大中小,都值得称道,都有特定历史地位。五四新文化人应感谢其论争对手,不管是林琴南、刘师培,还是胡先骕、梅光迪、章士钊,都是很有风度的正人君子,即便论战中占下风,也没有使用任何下三滥的手段。他们只是对新文化的看法不一样,对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思考有差别,所以在文化论述以及对新文化的判断上有差异,今天不应该都归为“敌人”。光谱扩大以后对新文化、五四运动会有新的了解。
当然我必须回到一个问题,这些都是名人,尊重他们的立场不一样,但大家请记得新文化运动中不幸落难的两个学生。大时代中有不同声音展开很正常,日后历史记忆中不同声音的代表者也会被关注,被压抑的是那些还没有成名的人和他们的论述。
请大家记得《新青年》上有关于旧戏的讨论,傅斯年日后大名鼎鼎都熟悉,论敌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张厚载,张厚载在《新青年》发的两篇文章,《“脸谱”与“打把子”》和《我的中国旧戏观》,谈中国京剧,这是一个戏迷,对中国京剧很有了解。在今天看来这是有专业色彩的对京戏的讨论。反而新文化人傅斯年写的《戏剧改良各面观》等文章,本身立场很坚定,站在西学立场,甚至他不懂旧戏,所以可以谈戏剧,因为不受污染。今天看来这个论调很可笑,不懂所以不受污染,可以谈这个话题。今天不敢再这么说。但是在一个西学占主流地位的时代,像傅斯年不怎么讲理地谈旧戏,反而被大家所接受。但是张厚载这个谈旧戏、喜欢旧戏的人却卷入北大的论争,被开除。
1919年3月31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上刊出校方的公告:“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、沪各报,传播无根据之谣言,损坏本校名誉,依大学章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,令其退学。此布。”就在毕业前三个月被北大开除。可以想象,如果成名的人跟北大论争,林纾没有关系,辜鸿铭没有关系,但是一个年轻学生、一个大四的学生即将毕业之前夕,被北大开除,可以想象他的处境很艰难。
为什么开除?因为他介入林纾和北大的论争。他读中学时是林纾的学生,上北大以后继续保持和老师的关系,替老师送文章,而且通信给报社,说北大里有内部矛盾,新派是谁,旧派是谁。《荆生》《妖梦》是他寄给上海的报社《新生报》,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,寄了以后,林纾觉得《妖梦》不太好,直接影射蔡元培,就不发了,他说来不及,已经寄出。他说“先生大度包容,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,当不甚介意也”。蔡先生没有说计较,但是把学生开除了。北大当时面临巨大的压力,舆情很严重,不得不有所表示。这个表示就是把不断写信给报社的中文系学生开除。
三年前,我们重新修订早年我带着学生做的《触摸历史: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》。我们把正面、反面、政界、媒体、大学的人物做了一本书,最早1999年出版,修订是2009年,再次修订是2019年,出版时加了十六个学生。五四是学生运动,但是在今天,主要的讨论对象是老师辈。其实学生也应该包括进去。他们日后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,我增了十六个北大的学生,最多的是中文系的,哲学系少一点。一个有趣的事情是,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是中文系,其次是哲学系,历史系没有多少声音,其他系也没有多少声音。
我增加的十六个人中,有一个人没有多少声音,没有多少成绩,历史书不会记载它,但是他体现新文化运动另外一个层面,他就是冯省三。他在1922年10月份被北大开除。他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、世界语学会干事,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世界语的,大部分是无政府主义的、反抗的、态度比较激烈的。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,北大上课都发讲义,鲁迅的日记说今天写完讲义,交给学校印出。印好以后放在课室里,学生上完课把讲义拿回来,学期末自己装订成册。但是这样每个学期学校的财政支出很大。蔡元培、陈独秀等人再三说,不应该发讲义,能不能买教材?北大老师们说,不行,外面的教材水平太低,根本不可能用外面的教材。能不能不发讲义呢?也不行。因为老师们的口音太重,学生听不懂。中文系教师大部分是浙江人,一直到三十年代,日本学者来这里听讲课,很伤心地说,我学了这么多年中文,到这里还是听不懂。旁边的中国学生告诉他,我也听不懂。怎么办?有讲义。我后来看鲁迅的讲义,这么少的文字怎么讲两节课呢?就是把讲义读一遍,然后海阔天空做很多论述、引申。1920年代讲义在北京大学很重要。
能不能收费呢?愿意拿讲义,就交一点钱,如果不愿意,没有关系。这就发生了学生暴动。围着校长办公室喊口号,老师们、校长出来,据说蔡先生挥着拳头说,我跟你们决斗。当天晚上校长辞职,院长辞职,教务主任辞职,各个系主任辞职。学生看不行,还是校长留下来,我们不再争这个事情。学校说不行,一定要处罚,但不能都处罚,那就处罚一个学生,这个学生就是冯省三。他自认当日确曾说: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!又曾说:我们打进(校长室)去,把他们围起来,把这事解决了!必须有人承担责任,于是就把这个学生开除了。
这个学生开除后到广东去,第二年就去世了,去世以后有三个人写纪念文章,一个是鲁迅,一个是周作人,一个是钱玄同。背后的思路,这个事情很特殊,一个风潮起来,必须有人承担责任,这个人就是牺牲。鲁迅说:“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,所留给大家的,实在只有‘散胙’这一件事了。”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:“牺牲为群众祈福,祀了神道之后,群众就分了他的肉,散胙。”蔡先生用这个办法,使学校重心回到正常轨道,在这个过程中,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牺牲。
比他更有名的另外一个人,是我的潮州老乡张竞生。现在很少有人熟悉他,但他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,后来被人称为“性学专家”。1922年美国计划生育的倡导者山格夫人来北大演讲,左右两边是北大哲学系的名教授,左边是胡适,右边是张竞生。当初在北京大学校园里,张竞生的名声不比胡适低,一个是留美讲杜威,一个是留法的学习卢梭,讲杜威的日后名满天下,学卢梭的日后举步维艰。这涉及新文化人努力的方向,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天花板。哪些是能说的、能做的、能努力的,哪些是陷阱,掉下去后很难翻身?我想说的是张竞生,这位北大的哲学系的名教授、法国留学的博士,当年他在《晨报》发起“爱情大讨论”时,新文化人大多是赞成的,鲁迅等人都支持。他出版《美的社会组织法》《美的人生观》都得到了周作人等人的欣赏。但是有一件事,征集出版惊世骇俗的《性史》,一下子就跌倒了。他1926年离开北大,来到上海,以为办杂志、办书店能够生活,其实很难。日后跟新文化人的距离越来越大,离开北大以后发展都很难,他在努力、在写作、在出版,但是在现代中国思想史、文学史上基本退场了。
当初新文化运动中,有几个重要的举动。北大组织了风俗调查会,有很多中国的风俗,大家都觉得很重要,需要调查,一共列了三十多项,其中一项是性史。毫无疑问正常的中国人都明白,一个民族的性生活的风俗习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话题,完全值得认真做,但是没有一个北大教授愿意做这个事情,这太危险了,张竞生是主任委员,他说,你们不做,我来。1926年2月2日他在《京报副刊》上刊出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——代“优种社”同人启事》,征求大学生的性经验,“请代为详细写出来”:“尚望作者把自己的‘性史’写得有色彩,有光芒,有诗家的滋味,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。”当把原来的社会生活调查、风俗调查写得有诗家的滋味、小说一样的兴趣时,问题就出现了。我们看到1926年出版的性史,前面的序言、后面的赘语是他写的。书出来以后举国轰动,一下被很多正人君子骂得狗血淋头,又有很多出版商紧急跟进,他很冤枉,说我就出了一本,后来的十多二十集都不是我弄的。别人把色情小说摘过来,仓促编成这样的集子,以后不断查禁。他是哲学博士,可是所有人都说他是性学专家,这个帽子戴了一辈子没有摘下来。
张竞生想学英国学者蔼理士,但没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,操作上出现大问题。他日后也承认,征文及选文的方向出现偏差,导致“《性史》第一集中未免有‘小说化’的毛病”,难怪时人将其作为淫书来抢购与阅读。虽说日后诸多续书乃不法商人牟利之举,与张竞生本人无关,但开篇没做好,科学性不够,这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,始作俑者,难辞其咎。
大家都说他日后很艰难,他受到守旧派的打压,我说打压他的其实是新文化人。为什么?他把本来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题目糟蹋了。潘光旦、周建人等也在研究妇女问题、性生活问题。但是他们做学术研究,不像他那样大张旗鼓。就好像一头大象猛然闯进瓷器店,他悠然转身,一地狼藉。所以大家对他很愤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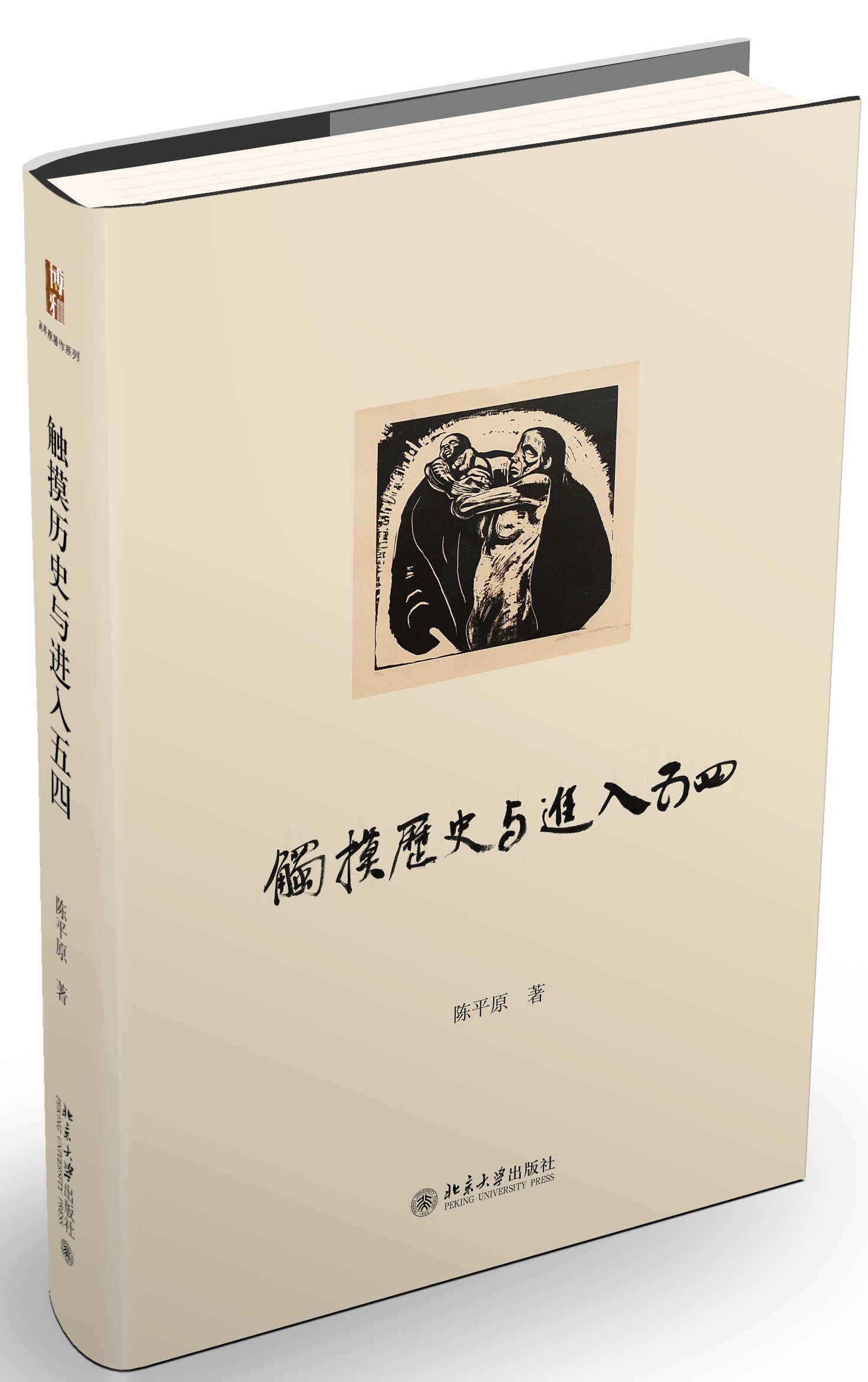
陈平原著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
我们看到在聚光灯下取得成绩的五四人物,但是在大的风潮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参与其中,包括后来被判定为反面,或者还没有成长就被打压,或者成名后走了歪路的人,所有这些人都应该纳入五四新文化运动考察的视野,这样对这个运动或者思潮的了解才会比较完整。
五四不仅仅是历史事件,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,还有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,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。因为它的正面性、重要性、丰富多彩,因为它不断被追忆而未完成,这句话隐含的不是所有的重要事件日后都能够不断被重塑和阐述。五四的好处是从1919年发生,1920年就开始纪念。1920年的纪念虽然主要是北大的老师学生纪念,后来拓展到全国,但是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把五四当作一个正面的、重要的历史时刻,不断跟它对话。五四的好处在于众声喧哗、生气淋漓。
我并不想在一本书里能让大家对五四有一个确定无疑的了解,我们的任务是,让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,引起世人的关注;在这个同样关键的历史时刻,重新审视五四。至于怎么关注,从哪个角度进去,得出什么结论,取决于个人的立场、视野、趣味,强求不得。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,是一个伟大的传统;以梁启超、蔡元培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为代表的“新文化”,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。某种意义上,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、反思、批评、拓展,更是当务之急,因其更为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,更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身立命。
五四对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,既是学术也是精神,某种意义上我希望这个话题不封闭在学院内部,不局限于现当代史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,而是希望它进入社会、进入公众,让非专业的人也能读,也能谈,也能参与这个话题,因为这个话题跟当下的中国文化走向,跟思想、脉络,以及对历史、对未来的思考有直接的关系,不管什么专业,这都是今天应该直接面对的话题,所以说五四是磨刀石。
陈思和:今天这个题目“三陈说五四”,应该改成“三陈说三书”,北大出版社出的平原的这三本书,内容很丰富,超出传统对五四的阐释,而且看到五四有趣的一面,看到正面也看到侧面,非常丰富,非常具有当下性。五四这个话题平原兄说最合适,他过去三四十年来的研究课题非常大,从晚清到现代,但是基本的核心都是围绕五四。

陈思和
谈五四,平原兄最有理由,传统说天时地利人和。从“天时”来说,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,平原兄长期工作在北京,对五四运动、新文化运动有深刻的理解。“地利”,五四运动主要发生在北大,当然还有很多学校,但以北大为主。平原兄基本上大半辈子都在北大工作,他爱北大,为北大编了很多书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,他编书宣传北大精神,目的是使五四精神能够被我们继承、发扬光大。再加上他那么勤奋,孜孜不倦,不仅研究五四运动正面的力量,也研究了反对面。
陈子善:我完全赞同思和兄的看法。去年上海书展,平原兄在这里有一个《有声的中国》发布会,里面也涉及五四的演讲,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人、演说家,也是从五四开始。
关于五四实在是讨论太多,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。我记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,当时有一个“文学节”就是定的五四,每年文化界都要开会谈论五四。

陈子善
平原兄的书很多,这三本书确实很吸引我。比如其中一篇《五月四日那一天》,下的功夫很深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各种不同的说法,报纸的报道,等等,很多历史的细节。很多人做学问都是大而化之,他把这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当时参加的那些人不同的说法都进行梳理。五四当天发生的事情怎么影响到后来,一直影响到今天。这样的研究从方法、具体操作层面,平原兄树立了一个榜样,我们可以借鉴、学习,从中受到启发。
陈平原:我长期在北大工作,所以研究会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帮助。我深刻意识到,仅从北大角度不够,我会自己再努力。
北大确实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1920年到1926年,每一年《晨报副刊》五四纪念都是北大学生做的。很长时间来,大家不觉得五月四日的游行有什么重要,北大学生一次一次的纪念让它的重要性凸现出来。五四是做出来的,五四也是说出来的,说出五四的意义是北大学生、老师的工作。5月4号发生的事件,5月6号北大教授开始出来说五四精神,20号罗家伦说五四运动的意义,等等。以后不断地说。这是北大做五四研究的好处。
这只是一个角度,一种眼光。这些年我带学生们努力拓展这个思路,我带着学生做各个学校。当初大学很少,中学、师范发挥很大作用,浙江一师、湖南一师、直隶女师,这些学校都在五四时成长起来。这些中学生,当初在整个大的运动中不是主角,在接下来的二十年、三十年,他们逐渐成为主角,所以走出北大的视野看五四,这是一方面。
我最近回答一个问题,怎么看朝鲜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系。我在韩国演讲经常会被问这个问题,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问题。我们关注1919年3月1号的朝鲜,也是因为外交纠纷引起来政治抗争,比中国惨烈得多,影响很大,是整个朝鲜近代史上重要的事件。两个月以后北京发生五四运动,有些重要的标识性的标语、口号、写血书等等都很接近,而且确实李大钊、陈独秀、罗家伦都支持朝鲜的三一运动,说明有关系,而且有启发。可是后来的论述不怎么强调这条线,原因在于从新文化入手,把5月4号发生的群众游行和此前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,和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联系起来,再跟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联系起来。这一条线联系起来,就淡化或者不关注朝鲜的三一运动跟我们的关系。
但是学术界一直在做这个事情,我查了很多文献,话题本身必须关注,不仅是北大的视角,不仅是中国的视角。几年前瓦格纳去世之前专门告诉我,他在美国发现一批档案,正在做,还没有做出来。当年美国驻中国的记者,他们如何穿针引线,帮助五四学潮运动。如果各位有兴趣将来读《未完的五四》这本书,建议读一篇《危机时刻的阅读、思考和写作》,只有理解那代人的所面临的处境,才能理解他们所做的努力,还有他们的论述。太平年代的书生在书斋里写文章、四平八稳的论述,和迫不及待、脱口而出的五四人的表达,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今天会有些人对五四不以为然。抓住五四那些人的具体论述,把它无限放大,以今天的学院的思考来判断,这是不对的。
不要高估五四那代人的学养,也不要低估他们求知的热情。在面对国家生死存亡急迫关头,没有那么多书生的考量。我们想象中的跟哪个大作家、大学者、思潮的联系,不是他们考虑的。他们考虑的是拿来就用,那些人、那代人,他们的学养、知识、思考很多是从媒体、报纸、杂志,而不是从学校、教科书上得来,所以表达直接、激烈、极端。今天阅读那代人的思考和表达时必须意识到,那是一种危机时刻的思考和表达,和太平年代的书斋生活是两回事。这样对他们某种论述中的疏漏、偏激、不妥,都会比较坦然接受。这样才能理解那代人,理解他们走过来的道路。
刚才子善说了一个有趣的事情,“文艺节”是国民政府定的。今天在台湾地区,还是五四文艺节,但是中国共产党在1939年把五四定为青年节,所以青年节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文艺节。这就是眼光高下,从文艺角度来谈新文化运动、文学创作,可以,但却局限在一个很小的领域,而把五四定为青年节范围扩大很多。不只是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,而是关乎整个政治、文化。国共两党如何面对五四资源?我引了《人民日报》和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不同时期的社论。这是一个大命题,政党必须抓住这个重要资源跟它对话,对话时自己也有回避。国民党为什么不愿意说青年?他们担心会引起学生的反抗、学潮等等,所以他们老是强调五四把社会搞乱了,但是五四的文学是很好的,新文学值得我们关注。从这条线走下去,始终在回避年轻人的诉求。某种意义上定五四为青年节,让我们意识到每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努力、困境、思考,始终是我们必须直面的话题。
对于年轻人的敏感性以及努力的方向,是我书里特别关注的。五四关注的是老师那一辈人,其实将来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是学生。北京大学国文系1917级的学生是将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,“同学少年多好事,一班刊物竞成三”。他们办了三个刊物,一个《新潮》、一个《国故》、一个《国民》。《新潮》是傅斯年、罗常培办的,《国民》是许德珩办的。这些杂志影响到中国以后的政治思想学说。他们当初小荷才露尖尖角,日后是他们的世界。所以要关注那些还没有成名,因为五四而觉醒的一代年轻人。
其实我们三位的思想已经固定下来,已经没有办法像年轻一辈敏感。五四那代人年纪比我们轻,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特别喜欢算账,他问我五四那一年谁最大?蔡元培五十一岁,鲁迅三十八岁,胡适二十七岁。当时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是二十多岁的那批人,是他们让五四生根开花。所以中国共产党定五四为青年节是有意义的,这才是未来。
谈论这个话题时,我希望不仅仅局限于学院的文章。我没怎么谈前面的两本书,前面两本书是用学院内部的方式做的,关于报刊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,关于物质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关系,这些都是学院里专注于此类研究的人所关心的内容。但我更关注的是五四运动能否继续与我们年轻一代对话。年轻一代对五四的关注不一定意味着喜欢它,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五四是一个必须对话的对象。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,人们可以批判、质疑、喜欢或不喜欢它,但大家都知道这是现代法国,甚至是现代世界的起点。因此,人们会不断与它对话,并调整自己的姿态。这正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。

陈思和:平原兄邀请我和子善一起讨论五四,这本身就体现了他所提倡的观点:五四是一个被言说出来的命题。我对这个观念非常支持。昨天我又翻了一遍《未完成的五四》,对其中的一个说法深感认同:任何历史事件都是通过言说而存在的。比如焚书坑儒,历史上被烧掉的书有多少?但正因为秦始皇焚书这件事被言说出来,才得以流传。而历史上也有许多重要的事件,因为没有被言说,最终被遗忘。所以,言说的力量在历史中是极其重要的。
平原兄说跟王瑶先生谈,王瑶先生跟着西南联大的一批人在谈。我导师贾植芳先生一谈就是鲁迅、胡风,那些人都是在教科书看到的,在他们嘴巴里就像邻居一样的,慢慢这种生活、精神、传统影响我们。到今天我们也七十岁了,要退场了。但是平原兄留下这个课题给大家、给学生、给学生的学生、给听众,接着谈。五四可以怎么谈,今天平原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今天没有谈鲁迅、胡适、陈独秀,谈的是辜鸿铭、林琴南,张竞生。不是说对这些人物大家更感兴趣,而是这些人物更好配合了五四言说。以前谈的人比较少,可能会更多给我们留下很多谈话的空间,其实这些人也有很多问题,但不是说一定要捍卫他才谈,而是对他感兴趣。我觉得应该有人继续来研究,不要用偏激的眼光看古代文学或新文化。
陈子善:我们有两个传统,一个是孔夫子下来的传统,一个是五四的传统,怎么面对、处理这两个传统,大家要继续努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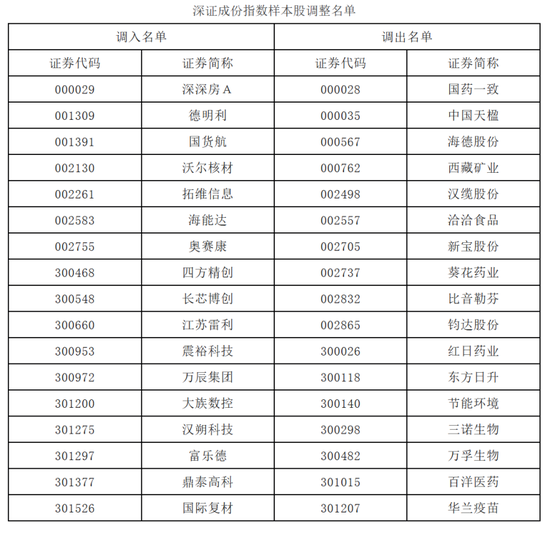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